郭晔旻 2024-07-2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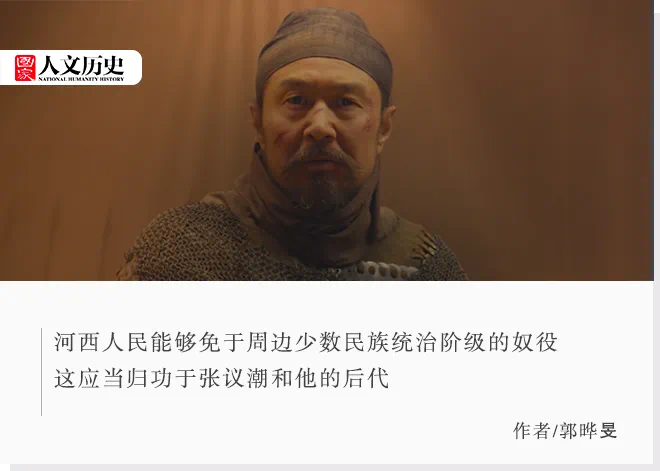
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(ID:gjrwls),未经授权请勿转载
河西沦落百年余,路阻萧关雁信稀。
赖得将军开旧路,一振雄名天下知。
——《张淮深变文》

莫高窟第94窟。此洞窟为张议潮的侄子——张淮深所开。即张淮深执权时期,为张淮深功德窟。来源/敦煌研究院
张议潮领导的沙州起义,对河西地区摆脱吐蕃奴隶主的掠夺和奴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作为起义的领袖人物,张议潮理所当然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评价。唐宣宗在诏书里称赞他是“窦融西河之故事,见于盛时;李陵教射之奇兵,无非义旅”。张议潮起兵之时,四面皆敌,孤立无援,他所面临的困难,要比窦融之辈多得多。故而人们称赞张议潮:
“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。四方犷捍,却通好而求和;八表来宾,列阶前而拜舞。北方猃狁,欸少骏之駃蹄;南土蕃浑,献昆岗之白璧。”
实在是位盖世英雄!
在敦煌莫高窟中,至今尚保存有一幅《张议潮夫妇出行图》,原作高120厘米,长1640厘米,是晚唐时期壁画艺术的杰作。图画描绘了张议潮收复河西以后,与妻子宋国夫人一起出游的盛大行列。图中不但有盛大的车骑随从和旗仗卤簿(古代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),而且还有百戏、仗乐、猎狩及人物的绘画,前呼后拥,极为壮观。从这一幅气势浩大的图画中,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位英雄人物的形象。

张议潮统军出行图(局部)。来源/敦煌研究院
诚然,历朝历代都有英雄人物,但在封建时代,张议潮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异数——以一己之力收复河西后主动向中原王朝输诚归附,这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实属罕见。诚然,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地方政权和平归附的例子,在张议潮之前,有岭南冼夫人主持归附隋朝;在张议潮之后,也有清源军(五代十国后期的一个割据政权。在今福建南部)与吴越国主动向北宋“纳土”。但这些事例,只是地方割据势力“识时务”的表现。岭南不降,难阻隋师,清源不服,能敌宋军?后果其实一目了然。但张议潮的情况跟他们截然不同,在张议潮收复河西之后,唐朝除了置军设使,以官爵羁縻之外,根本没有能力经营河西。十一州虽然归复唐朝,但宣、懿两朝都无暇顾及边政,只是名义上存在政府职官而已。张议潮若不主动归附,归义军政权凭借“西尽伊吾,东接灵武,得地四千余里,户口百万之家,六郡山河,宛然而旧”此等规模自立,李家朝廷又能有什么办法?
从这个角度看,张议潮归唐倒是有点类似南诏王异牟寻弃蕃归唐。只不过南诏虽然表示:
“牟寻曾祖父开元中册云南王,祖父天宝中又蒙册袭云南王。自隔大国,向五十年。贞元中皇帝圣明,念录微效,今又赐礼命,复睹汉仪,对扬天休,实感心肺。”
但异牟寻本人从来安居南诏,又岂能与张议潮“束身归阙”,留质京师相提并论呢?
另一方面,自张议潮于大中初年光复河陇至唐末,归义军张氏凡历三世近六十年。张议潮首创大义,使沦落百年之久的河陇地区人民摆脱了吐蕃奴隶主的残酷统治,屡次击败了吐蕃与回鹘等族的掳掠,维护了河西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自张议潮收复河西以后,一直到唐朝末年,河西人民能够免于周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奴役,这应当归功于张议潮和他的后代。
遗憾的是,张议潮固然在河西重振了大唐声威,但这个唐王朝,已然衰弱不可复振。起自河北安史旧地的藩镇割据,犹如恶性肿瘤一般扩散到中原腹心……距离河西重归版图不过半个多世纪,朱温代唐,中原进入“五季之酷”的乱世,更是无暇顾及孤悬河西一隅的归义军了。正是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下,河西历史经历一个短暂的插曲,即由“归义军”改制而来,以敦煌为中心的“西汉金山国”。关于建立它的起因与意图,敦煌学者中有一种颇为独特的见解,认为它的建国并不是针对中原王朝的,而是针对回鹘、吐蕃、羌、浑等周围少数民族贵族。当时这些政治势力不断对河西敦煌地区进行蚕食,阻断了敦煌与中原、西域的正常交往,敦煌已经陷于“四面六蕃围”的“孤岛”状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金山国的建立并不是脱离中原王朝的分裂割据行为,而是张氏政权奋起自救自振的行动。虽然这一尝试很快失败,但“归义军”作为一个汉人地方政权的地位,却一直持续到北宋中叶,最后亡于李元昊的西夏铁骑——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史诗电影《敦煌》所讲述的故事。

电影《敦煌》海报
归义军先后历经张、曹两姓氏族统治时期(中间还有一个短暂的索勋时期),历时一个多世纪。它的建立与存在,也成功逆转了吐蕃占领后当地出现的“吐蕃化”趋势,也就是所谓“百年左衽,复为冠裳;十郡遗黎,悉出汤火”。就行政区划而言,张议潮恢复了唐朝旧制,重建中原地区实行的“州县-乡里”制度和城坊制度。在恢复并改进乡里制的同时,归义军也恢复了唐前期实行过的城坊制度和坊巷的称谓。与此同时,归义军政权废除吐蕃时期的户籍、土地、赋税制度,重新登记人口、土地,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,制定新的赋役制度。在新税制下,赋税的名目主要有官布、地子和柴草三项。张议潮也废弃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,恢复了唐朝的都僧统制。一方面解放被吐蕃贬为寺户的良人,恢复他们原来的良人身份,使之成为乡管百姓,以增加归义军的财政收入;另一方面又调查登记寺院财产,设立都僧统司统一管辖,并规定任何人都不得侵夺损毁寺院所属的一切财产、人户。这些规定也赢得了僧侣们的信赖,保持了归义军政权社会的稳定。
此外,吐蕃的统治使得河陇地区的汉文化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敦煌文献《报恩吉祥之窟记》记载:
“时属黎氓失律,河右尘飞,信义川崩,礼乐道废。人情百变,草色千般。”
张议潮起义驱逐吐蕃守将后首先就“解胡服,袭冠带”。敦煌文书《辛未年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(一说是“蔑”)人状上回鹘大圣天可汗书》里记载:
“太保弃蕃归化,……却着汉家衣冠,永抛蕃丑。太保与百姓重立咒誓,不着吐蕃。”

莫高窟第159窟是吐蕃统治时期的代表洞窟。这个窟中保存着当时曾统治过敦煌的吐蕃国王的形象。来源/敦煌研究院
这段文字既说明吐蕃占领之前沙州百姓都着吐蕃衣服,也表明归义军建立后,即着手带领百姓摆脱吐蕃带来的这种影响(文中的“太保”即指张议潮)。这种“去吐蕃化”的行为无疑对恢复河陇地区的汉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使得整个河陇地区在经历吐蕃的长期统治后,恢复与增强了汉民族意识,汉文化得以留存和发展。而这,也正是“归义军”存在的最大历史意义。